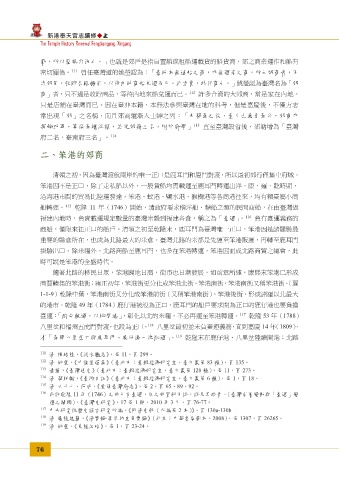Page 78 - 新港奉天宮志(上)
P. 78
新港奉天宮志續修◆上
The Temple History Renewal Fengtiangong, Xingang
載,所以監視出海也。」也就是郊戶是指自置船或租船運載貨的船貨商,郊之商業運作和船有
111
密切關係。 曾任臺灣道的姚瑩認為:「臺地本無造船之商,亦無運米之商,所云郊商者,不
出郊邑,收貯各路糖米,以待內地商船兌運而已。此坐賈,非行商也。」姚瑩認為臺灣名為「郊
112
商」者,只不過是收貯商品,等待內地來船兌運而已。 許多合資的大郊商,常是家在內地,
只是店舖在臺灣而已。因在臺非本籍,本無法參與臺灣在地的科考,但是嘉慶後,不僅方志
常出現「郊」之名稱,而且郊商還漸入士紳之列:「及蔡牽之役,臺人士義勇奉公,郊商亦
113
捐餉助軍。事後奏增泮額,並定郊籍三名,附於府學」 直至臺灣設省後,郊籍增為「臺灣
府二名,臺南府三名」。 114
二、笨港的郊商
清領之初,因為臺灣渡航兩岸的唯一正口是鹿耳門和廈門對渡,所以最初郊行僅集中府城。
笨港因不是正口,除了走私船以外,一般貨船均需載運至鹿耳門轉運出洋。康、雍、乾時期,
沿海港市間的貿易比陸運發達,笨港、蚊港、鹽水港、猴樹港等各商港往來,均有賴臺屬小商
115
船轉運。 乾隆 11 年(1746)開始,清政府要求橫洋船、糖船之類的民間商船,在由臺灣返
福建內地時,負責載運規定數量的臺灣米穀到福建各倉,稱之為「臺運」。 116 負有臺運義務的
商船,僅限來往正口的船戶。清領之初至乾隆末,鹿耳門為臺灣唯一正口,笨港因是諸羅縣最
重要的縣倉所在,也成為北路最大的米倉,臺灣北路的米都是先運至笨港販運,再轉至鹿耳門
掛驗出口。除米糧外,北路商船至鹿耳門,也多在笨港轉運,笨港因而成北路商貿之總會,此
時可說是笨港的全盛時代。
隨著北路的移民日眾,笨港闢地日廣,街市也日漸發展。如前章所述,康熙末笨港已形成
商賈輳集的笨港街;雍正初年,笨港街更分化成笨港北街、笨港南街,笨港南街又稱笨港街。(圖
1-1-9)乾隆中葉,笨港南街又分化成笨港前街(又稱笨港南街)、笨港後街,形成諸羅以北最大
的港市。乾隆 49 年(1784)鹿仔港被設為正口,鹿耳門的船戶要求開為正口的鹿仔港也要負擔
117
臺運:「酌分輓運,以均勞逸」,彰化以北的米糧,不必再運至笨港轉運。 乾隆 53 年(1788)
118
八里坌和福州五虎門對渡,也設為正口。 八里坌最初並未負臺運義務,直到嘉慶 14 年(1809),
才「奏開八里坌口與鹿耳門、鹿仔港一律配運」。 119 乾隆末在鹿仔港、八里坌陸續開港;北路
111 清 陳培桂,《淡水廳志》,卷 11,頁 299。
112 清 姚瑩,《中復堂選集》(臺北市:臺銀經濟研究室,臺文叢第 83 種),頁 135。
113 連橫,《臺灣通史》(臺北市:臺銀經濟研究室,臺文叢第 128 種),卷 11,頁 273。
114 清 蔣師轍,《臺游日記》(臺北市:臺銀經濟研究室,臺文叢第 6 種),卷 1,頁 18。
115 清 六十七、范咸,《重修臺灣府志》,卷 2,頁 65、89、92。
116 或許乾隆 11 年(1746)之前已有臺運,但之前資料不詳,詳見吳玲青,〈臺灣米價變動與「臺運」變
遷之關聯〉,《臺灣史研究》,17 卷 1 期,2010 年 3 月,頁 76-77。
11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,《明清史料(戊編第 2 本)》,頁 130a-130b
118 清 慶桂總纂,《清實錄‧高宗純皇帝實錄》(北京:中華書局影本,2008),卷 1307,頁 26265。
119 清 姚瑩,《東槎紀略》,卷 1,頁 23-24。
76